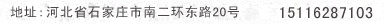法困土改只有底层改革创举却没合法性确认
法困土改:只有底层改革创举却没合法性确认
如果只有底层的改革创举,却没有合法性的确认,那么改革可能只是权宜之计,不能构成制度,没有长远的未来,也没法让各方对它有信心和稳定的预期 这一次,深圳恍如又走到了全国的前面。 2013年12月20日,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凤凰社区一块1.45万平方米的原农村集体工业用地,以1.16亿元的底价挂牌出让。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一个多月后,全国出现的"农地入市第一拍",并被舆论普遍解读为土地改革思路的现实注脚。 但是,深圳却异常低调。"这跟上世纪80年代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第一拍'的意义不可同日而语。"深圳市计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下称深圳规土委)1名不愿具名的官员称。 纵观深圳市近10多年来在土地改革上的探索,无论是2002年出台"两规"--对超出合法面积之外的私房处以罚款后,加以确权;还是2004年的"统征统转";或是2009年根据违法建筑的违法程度,进行分期分批处理的措施;直到最近调解土地利益分配机制的"1 6文件",其出发点始终着眼于"盘活土地"。 但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要"盘活土地",只有征地-入市一路可循。即使被誉为"改革排头兵"的深圳,土地改革也只能勉力触及天花板,难有真突破,距离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集体土地入市,乃至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仍是可望而不可即。 农民的觉醒 凤凰社区地块,位置极优越,紧临107国道--这条道路不但连接广州和深圳,更一直向北沿伸至北京。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推敲如何利用好这块地。"凤凰社区党支部委员文永昌说。在寸土寸金的深圳,这块土地已闲置了30余年,这不是他们的本意,而是缺少市场化利用的途径:想要合法利用这块土地,只有一个途径--交给政府,再挂牌出让。 凤凰社区曾推敲过在这块土地上建设"小产权房",这样做的好处是收益都能留在集体内部,但其不合法性带来的风险,终究让社区的领导班子打消了动机,直到深圳市"1 6文件"出台。 2013年1月8日,深圳市政府出台"1 6文件"。与现行法律框架下的土地收益分配方式不同,这份文件改变以往将土地收益全部收归政府,只给原村民征地补偿的方式,转而设置了两个选项:一是将土地出让所得收益的50纳入市国土基金,另外50归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继受单位;二是将所得收益70纳入市国土基金,30归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继受单位,但可同时持有不超过总建筑面积20的物业,用于产业配套。 凤凰社区终究选择了第二种方式。"具有物业,可以稳定收租,我们计算过,与自己建厂房出租的收益差不多。"文永昌说,另外,集体还可以获得3000多万元的土地出让金。 "凤凰社区真是'惜土如金'。"终究拍下凤凰社区地块的深圳市方格精密器件有限公司(下称方格公司)董事长王平说,从2007年公司落户凤凰社区后,他曾多次询问租用的厂房是否是出售,但社区负责人历来都避而不谈。凤凰社区共有260多家企业在册,此次竞拍成功的方格企业是其中之一。 "有些企业在我们这里壮大以后,就'飞'走了。"文永昌说,所以社区一直在琢磨怎样和社区内的优秀企业联合在一起,以便长时间共同发展。 2004年,深圳宝安区土地全部转为国有时,凤凰社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参照《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改制成立凤凰股份合作公司,主要业务就是经营村集体资产。"1 6文件"出台以后,凤凰社区与正在酝酿上市的方格公司主动接触、谈判,终究达成由凤凰社区股份公司出资购买该企业7.5原始股的意向。 "凤凰社区的想法非常明确,如果竞拍中有企业能出更好的条件,那这块地还不一定是方格的。"王平说。 作为"1 6文件"发布后的第一个试点,凤凰社区一直都保持着对土地资源控制权的高度警惕。由于试点需要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因此社区必须在土地招拍挂前与政府签订土地"征转协议",但社区明确要求协议标明:如果拍卖未能成功,则土地仍然交还原村集体组织。 总结之前30年的被征地经验,再权衡现实中土地价值增长,使得"寸土不让"已成为原村集体组织的一个共鸣。 谁来算 2013年12月20日上午,凤凰社区地块拍卖之前几个小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深圳市规土委举行了一次讲座。席间有人提问:政府在土地收益上多次让利,但为何仍然没法获得社区的响应?周其仁答:"别替他算,我们算不清楚,让他算。" 1句"让他算",点出了土地资源配置中谁是主体的要害。在力主土地制度改革的人士看来,依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方向,政府应当将土地资源配置权让渡于市场。不过,这1观点在许多地方政府看来过于激进。乃至深圳市一些官员也认为,逐步优化利益分配机制,渐渐释放出部分产业用地,是目前最为稳妥的改革方式。 因此,这次凤凰社区的拍卖,依然遵照征地程序,通过签订征转协议,完成土地国有化的手续,出让主体仍然是深圳市政府。在社区看来,这与通常的征地并没有根本辨别,难言市场化。 但是,在深圳乃至全部珠三角地区,其过往发展正是得益于集体经济组织对土地的自主开发。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伴随着深圳特区经济突飞猛进地发展,在宝安、龙岗两区经济较为发达的村镇,农民们自行进行了"城市化":几近所有的农地都被用于工商业开发,农民们也都洗脚上田。 20多年来,绝大多数深圳农民的收益已不再来自农业生产,几近完全依赖于土地出让、私房出租和从集体土地开发中所获得的红利。这些面积巨大的"已建成区"虽有违《土地管理法》,却已是既成事实。 至2004年,深圳市推行"统征统转",此举属于在征地制度大框架下的一次法律突破,也再次确认了此前对"已建成区"的处置办法:政府承认农民对"已建成区"的土地使用权,也不追究违规;但同时必须把上述两区"已建成区"土地的权属统一转为国有,并不再对农地征用作出任何补偿。这1模式下,农民虽可"免交地价款",继续享有"已建成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收益,但同时也永久丧失了本属自己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 时至今日,深圳存量土地几被开发殆尽。据深圳市公布的数据,至2011年,该市实际用地到达934平方公里。按此计算,尔后9年间,深圳唯一42平方公里土地可供使用,如以每一年10平方公里的速度开发,5年以后,就将无地可用。 为减缓用地瓶颈,深圳市政府相干负责人一度提出"政府要有勇气配置土地"。相邻的东莞市也提出"镇里要勇于向村里统筹拿地",以至于很多观察者认为,珠三角地区正日益"内地化",已失去了昔日改革先锋的锐气。事实上,对深圳来说,土地出让金收入在市级财政占比只有不到20。但是,如果失去了土地资源配置权,在争取某些国企和国家大项目上极可能落于下风,产业竞争中,也难于摆脱以土地作为招商引资的筹马。 同时,在梳理存量土地进程中,深圳发现原农村集体用地数量极为可观,共占用约390平方公里建设土地。但合法用地唯一95平方公里。 没有合法身份的这类土地,大多以违法建筑用地及工业用地两种模式存在。以村集体组织和自办股份公司兴建的房屋或是由农民自行组织建造的住房,虽然其所在土地已属国有土地,但因没法进行产权登记,民间仍然称其为"小产权房"。 "由于没有合法的手续,现在的结果就是政府用不了,企业用不了,村里也用不了。"深圳市规土委的官员介绍。 在此背景下,2013年初出台"1 6文件",指向相对容易盘活的工业用地,躲避了更为人所注视、范围更大的"小产权房"。深圳规土委人士泄漏:"假定可以妥善处理此类工业用地,经验可以拓展到公共设施用地、商住用地,乃至连片的既有空地又有建筑(包括违法或不违法建筑)的用地。" 面对已意想到土地价值且实际控制土地的原集体经济组织,"1 6文件"选择淡化征地痕迹,将一些组合"让利"的方式引入收益分配环节。 但对土地实际控制者来说,这仍是与政府的博弈,而不是与市场的博弈。 法外世界 2011年时,在深圳一次土地改革报告会上,1名基层官员提问:"怎样解决根本性突破的改革与现有法律的衔接问题?"预会的周其仁回答,这要看深圳市政府的魄力和勇气。 实际上,自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订实行以来,集体建设用地入市面临着难以逾越的法律障碍。 《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出租用于非农建设"。对非法批准、占用土地等行动将追究刑事的规定,更是悬在地方政府头上的一把利剑。 即便是改革先锋之地的广东省,其2005年6月以政府令的情势颁布的《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也没有突破以上法律框架。 深圳土改在法律意义上的一次突破性的尝试,就是2004年的"统征统转",事实上它是对《土地管理法实行条例》第二条第五项的奇妙解读,这项规定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部成员转为城镇居民的,原属于其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即转为国有。据此,深圳将宝安、龙岗两区内的27万农村人口一次性转为城市居民,从而一举将两区956平方公里土地转为国有。 国土资源部对深圳的做法最初持反对意见,并在2004年下半年派小组赴深圳专项调查,终究定调为"不宜模仿""下不为例"。 2005年3月4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国土资源部发布"国法函【2005】36号"文件,对《土地管理法实行条例》第二条第五项作出专门解释,明确该项规定,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被依法征收后,其成员随土地征收已全部转为城镇居民,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剩余的少量集体土地可以依法征收为国家所有。 根据这1解释,只有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逐渐被依法征收,并全部转为城市居民后,才能对农民集体剩余的少量土地转为国有。这其实是对深圳的"转地"法律依据的否定,也断绝了其他地方效仿深圳市"统征统转"的可能性,深圳成为了真正的"特例"。 尔后近十年,深圳在土地改革上,再未出现重大突破。其遵照的改革路径,也开始强调规则:一般先地方立法,或由政府文件、部门规章制定规则,再安排试点以使其有法可依。2013年初"1 6文件"的制定,更事前取得了国土部与广东省的特许。 中国现有的土地法律框架是基于《宪法》第10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除法律规定之外,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这构成土地制度的基础。倘若享有同等权利,两种土地所有制,乃至多种土地所有制,其实并不会引发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 从1986年颁布的《土地管理法》开始,农村集体土地的产权就已被施加了多重限制,要求农村的土地,不管是农用地还是非农用地,不经过征地程序转为国家所有,不能成为城市建设用地。1998年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进一步缩小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利用空间。"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农民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发展经济,和土地农转非有相对便利的环境,到1998年《土地管理法》实行后产生了根本改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刘守英说。后来的法律框架事实上取消了村集体组织经营土地的权利。 改革没有大突破,但深圳农民已自发将土地出租或在土地上建厂房、仓库、店铺出租,渐渐演变出一个"法外的世界"。在深圳,截至2010年7月,历史遗留违法建筑共35.7万栋,总面积3.9亿平方米,分别占全市总建筑栋数的57.5、总建筑面积的47.6。 对如何将这个热烈的法外世界纳入到合法框架里来,深圳市做过很多努力,多宗本地规章都提出,只要补交一定地价款并符合相关规定,可推敲给予法外业主确权,并发放可入市流通的产权证,但应者寥寥。 "不办理那个产权证,这块地就永久是我的,而办理了产权证,就只是几十年的使用权,为什么要去办?"深圳宝安区一名村民说。政府的种种举动都被原村集体组织理解为"拿地",并担心自己将失去对土地资源的控制权。 破茧寻路 "客观上讲,经过30年的发展,如果没有一个保护机制,是没有人愿意去做突破性的改革试点的,由于风险太大了,这点与上世纪80年代不同。"深圳市1名国土系统的官员直言。 上世纪80年代土地制度的改革一样面临着压力,要冲破土地资源高度严格的计划管制,改变任何建设用地的需求,都要经过政府征用、划拨的情势来获得满足。1987年12月,当深圳敲响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第一槌"时,乃至一度被当时的舆论认为是"卖国"。实际上,此前的9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已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出让、转让,已为"第一槌"提供了法律支持。 随后,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原文第十条第四款"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以其他情势非法转让土地"中的"出租"2字删去,并增加"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的规定;随后修改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再到1990年国务院发布《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成片土地暂行管理办法》。 可以说,在突破土地资源计划管制,城市土地使用制度逐步实现了从无偿、无限期向有偿、有限期使用的转变进程中,不管之前还是以后,都迅速取得了法律层面的认可。 但需要看到,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对象是对土地资源的计划管控,各界认识比较统一。而目前土地改革所依附的利益巨大,难以像当年的改革那样构成共鸣。在法律层面进行修改,给予改革者合法的鼓励就变得更加迫切。 "中国改革有一个不错的传统,就是通过改革试验区,让一些地区先行先试,争取某些突破。但是先行先试,没有法律障碍的还好办,如果与先存在的法律法规直接冲突的,就很麻烦。强调有法必依,改革就只好搁置。允许突破,依法行政又怎样交代?所以这些年试验区很多,但真正要改出花样来也确切很难。"周其仁在2013年11月12日的天府峰会上表示。 周其仁指出,如果只有底层的改革创举,上层迟迟不给予合法性的承认,那这项改革顶多只是权宜之计,不能构成制度,也没有长远的未来,让各方对它有信心和稳定的预期。 改革需要变法,一样需要遵照法律程序。此前包括深圳等地的改革试点,大都是通过向部委争取政策得来。"1 6文件"就是经国土资源部许可出台,时任国土部部长徐绍史还指出,要"严格审批、局部试点、封闭运行、风险可控"。 但是,深圳市的这1努力,也被认为是"违法的改革"。"在中国现行的法律体制下,《土地管理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无论是国土资源部,还是广东省政府,都无权授权深圳市违背《土地管理法》进行改革。"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程雪阳撰文称。 在他看来,上海自贸区的试点程序应当成为地方试点的标准程序。上海自贸区经国务院申请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3年8月30日授权国务院,未来三年,在自贸区内暂时停止实行有关法律规定,如医治白癜风要多少钱《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3年后,实践证明可行的,应当修改完善有关法律;实践证明不宜调解的,则恢复实行原有法律。 周其仁也认为,上海自贸区开辟了新路径,即依法授权突破,明确一些全国性法律法规在某个范围内暂停使用。 土地改革试点如能一样取白癜风缘由得法律授权,在试点范围内暂停政府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法律依据,探索集体土地有偿出让的制度建设,改革试点可能会发挥出真正价值。 对辖区面积10.7平方公里的凤凰社区来说,由原村集体组织控制的土地还占绝大多数,而他们仍然会继续寻觅合法的利用途径。 回顾国有土地有偿转让制度的演进进程,从1987年将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引发宪法修订,再到《土地管理法》等相干法律的确立。在这1重大的制度变迁中,谁终究代表国家出让土地,出让的权限怎样划分,谁具体组织土地出让,土地出让收入如何分配等重要事项,都经历了从模糊到逐步清晰的进程。如今,集体土地如何入市,如何实现"同地同权",一样有诸多困难待解,其间并没有捷径,唯有在实践中摸索。从这个意义上说,破除禁锢改革的种种法律障碍,进一步激起改革活力,已属当务之急。
- 上一篇文章: 本周央行公然市场净投放415亿元
- 下一篇文章: 环保大会召开作出重要部署